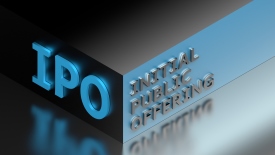乔焕然
植德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在加入植德之前,乔焕然律师曾在数家知名律所工作。专业方面,乔律师已从事律师出庭业务二十年,特别擅长涉外仲裁,经常活跃在ICC、LCIA、新仲、港仲、贸仲、北仲等各商事仲裁院,以及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亦担任海南国际仲裁院仲裁员。乔律师能用英文直接提供出庭服务。行业方面,乔律师聚焦于TMT、物流、汽车、新能源、海外贸易与建工等行业,代表客户包括微软、滴滴出行、新美大、商汤科技、新飞通等。乔律师也是破产衍生纠纷解决专家,经办此类项目的标的额已超过五十亿元人民币。此外,跨境合规也是乔律师的专长之一,出色地处理过有关FCPA(美国《反海外腐败法》)、EAR(美国出口管制法规)以及中国《数据安全法》项下业务。
乔焕然律师曾多次获得国际法律评级机构及专业法律媒体颁发的各项殊荣,如The Legal 500“争议解决2022年度特别推荐律师”,《商法》2020年度、2021年度“The A-List 中国100位法律精英”,以及LEGALBAND “2021年客户推荐15强律师(汽车与新能源行业)”等。
专访内容
Q1:作为一名深耕商事争议解决业务二十年的资深律师,在您看来企业客户为什么会更青睐仲裁这一纠纷解决机制?能否结合您以往的具体案例谈一下您的看法?
乔律师:
首先,仲裁不同于诉讼,不属于国家制定的诉讼程序体系而是属于Alternative Disputes Resolutions(“ADR”)即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的一种。换言之,仲裁这一争议解决机制的发明者并非哪个民族国家的立法机关和政府,反而源于民间商业交往。所以从程序渊源角度而言,仲裁源于民间,是商人们因为商业交往而产生、发展的,民间和商人对仲裁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我个人进一步认为,仲裁法律制度,同其他的商法制度(比如《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实体商法)一样,都属于商人群体的自治法律,只不过仲裁法律旨在指导商人们在解决商事纠纷过程中的程序问题。商人们经商时难免不会产生商事纠纷,他们的自治性特征很多时候表现在他们更倾向于“私了”而非“公了”,即更愿意找商事群体内部的行业人士来断案,而非到国家诉讼机构——法院寻求解决,这就像商人们往往更加看重商业法律惯例,比如他们喜欢使用《国际贸易属于解释通则》来解决国际贸易的风险负担、保险、运输等实体法律问题,喜欢使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来解决国际贸易支付这一实体法律问题一样。须知,这些实体商法只要经过商人们在合同中约定,便立即得到民族国家制定法律的认可,根据“有约必守”的原则去履行。同样,仲裁也不例外。只要商人们约定了仲裁这一机制,那么它便立即独立于包含它的主合同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合约,商人们一旦出现纠纷也会根据“有约必守”的原则去履行这一份属于程序法性质的争议解决合约。所以,它对于商人群体的天然亲和力及其更能体现商业独立经营特性的自治性优势,决定了企业客户在国家法院和仲裁机制之间更倾向于选择仲裁机制。举例而言,我本人从事中国涉外律师这些年中,屡屡发现跨国公司对中国法务律师有个基本要求:在选择争议解决机制时必须适用仲裁而非法院,除非遇到例外情形(比如存在“可仲裁性”障碍)。究其原因,应该说本质上这还是商人自治的要求。
其次,企业客户是典型的商人群体,它们每时每刻必须将“营业”作为新陈代谢的基本活动,就像我们自然人的吐故纳新的呼吸过程一样。这就决定了,商人群体在营业过程中必须找到一种更合理的途径/方式来解决他们时常会遇到的商事纠纷,而这些纠纷本身就是“营业”所注定要出现或预防的客观实际。换言之,“打官司”就变成了“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打官司不是商人的价值取向,因为这与他们所奉行的“和气生财”“合作共赢”的非零和游戏商业本质格格不入。所以,从某种角度讲,到民族国家法院去诉讼,并且还要满足社会公众对于诉讼这一司法活动的监督/公开性,与商人之间的非零和游戏的合作/营业是存在矛盾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有个出口即另一套方案/产品提供给商人群体。这套产品就是仲裁。因为仲裁具备诉讼无法比拟的自身优势:第一,仲裁裁决畅通于全世界,全球执行,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1958年《纽约公约》。根据公约的要求,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承认商人群体之间的仲裁合约和仲裁裁决。相反,没有哪个民族国家的法院判决书能够有如此广度和深度的国际承认,这样也同时解决了不同国家之间商人在争议解决过程中的信任机制问题,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各自任命各自的仲裁员,再进而由两个仲裁员去决定第三位首席仲裁员的机制来解决信任危机,从而避免A国商人不相信B国法官(反之亦然)的信任问题。第二,仲裁过程对外保密。除非仲裁合约有例外规定,否则一般情况下仲裁过程及其产品——裁决均对外界保密。我们知道,商誉对于商人而言至关重要,而且也不能因小失大,在解决纠纷时也仍然需要继续营业,甚至不能影响双方的相关合作。这样,就产生了保密的需求。但是在法庭那里,同样难以满足保密需求,因为诉讼讲求的是以公开审判为原则,保密反而是例外情形。举例,我本人自2018年开始处理一件国际仲裁案件,这个项目如果是法院判决就难以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项目涉及中国内地、香港地区、美国加州、菲律宾四个法域。没有哪个法域的判决书可以有把握在四个法域内畅行无阻,而仲裁却可以。
再次,仲裁还有其他诸多优势,比如它讲究“一裁终局”,也就是说一锤子买卖,没有上诉机制。这一特点充分满足了商人营业性的本质要求,换言之,速战速决讲求效率,打官司不要影响做生意。这一优势如果运用得当,商人就会节省大量时间/费用,实现与诉讼相比的高性价比。再比如它还讲求“灵活性”,不但不会依赖国家所制定的《诉讼法》《诉讼证据规则》,反而还允许商人自己来约定小到“举证期限”大到“适用法”的方方面面,从而充分反映出商法自治的特征。举例,我本人曾在为一件商业交易草拟仲裁合约时根据项目需要,在该合约条款中特定设立了一个“仲裁审理期限”的条款。该条款要求的裁决期限为仲裁庭组庭后60个自然日而非大家在诉讼中常见的3个月或6个月的法定审限。果然,当后续出现纠纷时,双方有约必守,而仲裁庭也据此在60日内作出了裁决。
Q2:正如您所言,仲裁确实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且作为国际通行的争议解决方式也备受各国推崇。近年来,我国香港、北京和上海也纷纷入选全球十大最受欢迎的国际仲裁地。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以及中国仲裁的国际化之路的?
乔律师:
的确,我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近年来在国际仲裁的“仲裁地”排名中稳步上升。这实际上反映了其背后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事实。正是因为与中国具有连接点的国际商贸、投资往来越来越频繁,所以中国仲裁话语权才不断提升。所以,近年来中国仲裁国际化也成为业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对此,我个人有几点想谈。
第一,中国虽然已是仲裁大国,但尚未成为仲裁强国。所谓仲裁强国,是指不但数量多,而且解决问题的质量高,全世界的商人都从内心里相信中国的仲裁机制,都愿意在仲裁合约中选择中国仲裁,放心地把未来/当下的纠纷放到中国来解决。在仲裁界,“仲裁地”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仲裁的产品——“仲裁裁决”的国籍问题。我之所以讲我们还不是仲裁强国,是因为我们在处理国际仲裁项目时往往发现绝大部分国际仲裁的仲裁地并非中国而是选择了海外,比如仲裁地位于巴黎的国际商会仲裁院(“ICC”)以及位于伦敦的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十几年前,我在办理第一件国际仲裁时就发现一个与我们中国做法不同的现象,在一起与英国根本没有任何连接点的国际商事合同中,双方选择的未来纠纷解决的仲裁地“竟然”是伦敦。当时我比较惊讶,使我认识到为什么伦敦会成为国际仲裁中心。
第二,中国要成为仲裁强国,其国内仲裁法就不得不融入更多的国际因素。在业内,大家所熟知的1958年《纽约公约》颁布至今已经有六十多年,其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85年主持制定了《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示范法”),从此全世界很多国家/地区的国内/区域内的立法趋势都是学习、参照示范法,进而形成自己的国内仲裁法。这些国际/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示范法家族”,彼此之间的仲裁语言越来越相互融通,更容易彼此理解。比如,我国香港地区自2011年修订《香港仲裁条例》以后也进入到了示范法家族,使得原本就具有普通法优势的香港仲裁更有吸引力。所以,我们在修订《仲裁法》时也不妨进入到示范法家族,取得与世界更多的共鸣。
第三,中国仲裁国际化的发展根本还是在于人才的培养。必须承认,我们的人才培养到目前为止仍是短板。但令大家欣喜的是,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伴随中国企业“出海”的脚步,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律师通过刻苦学习、苦练内功,已经呈现出逐步开花结果的良好态势。而且还有一些心怀祖国的“国际仲裁大家”,比如香港地区的杨良宜老师等,都在通过各种形式,努力探索中国仲裁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坚信,中国成为仲裁强国不是梦想而是一个切实可以实现的理想,当然这需要我们中国仲裁人的集体智慧和持续不断的努力进取。
Q3:您认为,成为一位优秀的争议解决律师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在这条路上,您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乔律师:
关于特质,首先,必须要有对于争议解决尤其是仲裁业务的热爱!没有热爱,很难长期在这一领域坚持。这种热爱应当出自心底的一种执念,把每一个争议解决案件都当作一个学习和提升自己的阶梯,而不是一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
其次,热爱需要持久和坚持。这个世界永远不缺乏诱惑,缺乏的是在抵制诱惑上慎始慎终的坚持。在国际仲裁这一争议解决领域,据我所知,能够成为国际公认的“大家”无不具有对仲裁那种发自内心的持久热爱。我个人读书有限,但是有几位老师的书籍使我受益匪浅,我在此也推荐给大家。第一是杨良宜老师的两卷本《仲裁法》,杨老师深耕国际仲裁四十余年,是华语世界极少有的学贯中西的大家;第二是Alan Redfern老师的《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Redfern老师纵横国际仲裁六十余年,其著作中那种力透纸背的力量令我着迷;第三是Gary Born老师的两卷本《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这本书可以说是国际仲裁的百科全书,我们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几乎所有课题均能在其中寻得钥匙。
关于所谓努力,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自幼读书以来,只是保持一个手不释卷的习惯而已。